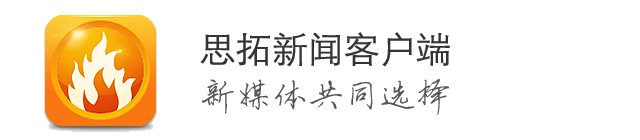云上木林
□ 杜旭元
春日在花端,金秋在云上。木林,就是一个在花端云上的地方。
春日众花接踵而来:桃、梨、苹果以及麦子、玉米、糜子、荞麦都开花了——木林在花端。秋季水汽氤氲,白雾成云,云把沟装满,将塬面覆盖。看去满塬只有几个屋顶、几根树梢、个别人影儿——木林在云上。
芮地像一个手掌,木林是手掌的一指,指向东南。县域的南北二塬像两根扁担,担起了一方百姓的饭碗。和木林隔水相望的柏树塬,也在扁担的东头儿,都是崇信的良田沃土,都是太阳一出来就照到的地方。而木林地貌丰富,像个啥呢?像片桑叶?像朵绿云?它确是许多绿色云朵儿组成的,许多云朵似的梯田小山组成了岭,连成了塬。一道塬,两条水拴着,四股风吹着。东风吹来的时候,花就开了,果实就开始结了;南风吹来的时候,天就下雨,庄稼就茁壮成长;西风吹来的时候,玉米、糜子、树叶儿就黄了,秋收冬藏;北风吹来的时候,就下雪了,天地一片银装素裹,人们便足不出户。木林在梦里。
我是第一次来木林采风,为木林塬画像。我们的主题是:《大美崇信·写意芮鞫》——红色记忆采风走进木林。木林是崇信红色记忆的源头。1935年秋,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木林,被国民党三十五师围追堵截,之后在金龙村与尾追至大庄村的国民党骑兵团隔沟打了一仗,并当即在金龙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,确定了北上方向,然后迅速撤离。一些艰苦细节写在我的短篇小说《枣木匣子》里,还写在《岭上桃花》里。至今,那堵布满枪眼的土墙还在,金龙庙还在,成了红色教育基地和国家3A级旅游景区。
看着大柳树下的英雄群像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,我的心头不禁冒出了一句:一群背着光跑的人!是啊,是他们为我们背来了今天的光明。
缅怀先烈,回望当下。金龙村已围绕红色基地推动了“红色景区+康养旅区+产业园区”融合共建,开发出了窑洞展馆、农家乐、游乐场、核桃林等产业项目。走出村部时,我看见大门口有两棵树,一棵是玉兰,一棵不是玉兰。此时花已落,叶已盛,它们都结出了一树的“毛笔头儿”,一个毛茸茸,一个很光洁。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。
在采风中我发现,各乡镇都有红牛,都在窑洞养牛。不过大庄村的牛犊“果子”大,结得稀,像卸了袋的苹果,等着成色到了采收呢。
车到一片玉米地边,一台收割机在采收青饲料,后边两个翻斗车轮流拉运。摄影师们又一窝蜂地去了,我们几个就在一棵核桃树下的草里找核桃,有说捡到绵的,有说捡到格的。我说核桃格绵可以调整:格了,砍几条树股就绵了;绵了,砍几条树股就格了。他们都不信。
村庄的人虽说少了,有些寂静,核桃树把路都夹窄了,大巴有些挤不过去。但生活物资却很富裕,不出钱的东西什么都有。我看见一家门口的渠边上有一小畦韭菜,都出苔了,全部开着白花,密密麻麻。是人少吃不了吧?有几只被秋风吹白的蝴蝶儿在上面飞舞,七上八下,没有声息,它们的体力可能和阳光一样轻,四处透露着农家寂寞的味道。
木林村部西侧有一大片香菇棚,是一家企业种的。棚里菌棒层层高叠,像蜂巢。香菇很繁,像一茬盛开的花儿,花儿一齐开了,采也采不完。我们中的几个人都买了,买的是新鲜的香菇。香菇棚的隔壁是酿酒的,酒的成色很好,金黄透亮。工作人员打开一瓶叫我们品尝,我刚端起一盅要尝,一只小黄蜂飞来和我争酒,我赶忙咂了一下。可等我再次低下头时,一只蜂儿已在杯里,另一只也前仆后继地跌了进去。摄影师立即抓拍,大家哄笑不止。蜜蜂不作假的,尤其是精明的野黄蜂。说明这酒的品质不错,是地道的土蜜黄酒。
木林的种植业有苹果、核桃、花椒。养殖业有牛、有猪、有鸡。鸡在东杨寨村尽头的一个深沟里。沟被一片密密匝匝的洋槐林长满、长平,林下全是鸡,不知其数。它们是红瑶鸡、五黑鸡、贵妃鸡、瓦灰鸡、珍珠鸡,全是奇鸡怪鸡。沟边的平地上有母鸡数舍,公鸡一舍。母鸡多为黑色,像非洲姑娘。公鸡独圈,皆红氅艳冠,戴着眼镜,神气十足。林下的母鸡群里夹杂着几只大雁,几只大鹅,一伙鸭子,不伦不类,叫声各异。那个女乡长告诉我:养大雁和鹅是为了给鸡看家护院,如果有大鸟、狼狐什么的,它们会报警,甚至直接出手。
木林不负众望。地上的、树上的、棚里的、沟里的都是财富。写在信小刚书记给我的规划里的和长在农户田园里的,重合在了一起,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木林:万亩果园,万头红牛,20余亩菇棚,以及小麦半塬、玉米半塬,花椒、核桃不计其数。